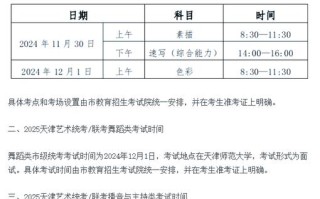光影之外,声息之间——我的北电艺考纪事
北京,冬天的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子,毫不留情地刮过脸颊,我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羽绒服,站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,仰望着那块刻着校名的巨大石碑,阳光斜斜地照在上面,反射出冰冷而坚硬的光,那一刻,心中百感交集,仿佛三年来所有的坚持、所有的怀疑、所有的期盼,都凝结在了这方寸之间的寒意里。

我叫林风,一个来自南方小城的普通高中生,我的世界,曾一度被框在书本和试卷的方格子里,直到高二那年,一部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,原来,电影可以这样讲故事,可以这样探索人性的深渊,可以这样用光影编织梦境,我第一次意识到,那块闪烁的银幕背后,是一个由光影、声音和思想构筑的广阔宇宙,从那天起,一颗名为“导演”的种子,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。
我的艺考之路,是从一场孤独的远征开始的。
为了备考,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活动,同学们在周末打球、逛街、谈恋爱时,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一遍遍地拉片、写影评,我分析了库布里克的每一个镜头构图,研究了王家卫的色调美学,背诵了无数经典剧本的台词,我的书桌上,除了五三,电影艺术》、《故事》、《认识电影》这些大部头,我的父母起初是反对的,在他们看来,那是一条比高考更不确定、更虚无缥缈的路,我至今记得父亲和我那次激烈的争吵,他拍着桌子说:“林风,你要现实一点!搞艺术,饿不死也发不了财!”
我没有争辩,只是默默地拿起手机,给他看我在豆瓣上发表的影评,看那些陌生网友给我的点赞和评论,我告诉他:“爸,我不是在玩,我是在学习一种语言,这种语言,我想用一辈子去说。”或许是看到了我眼里的光,或许是妥协于我的固执,他们不再反对,只是默默地为我凑齐了那笔不菲的培训费和考试报名费。

在省城的艺考培训机构里,我见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“同类”,我们像一群被命运召集的信徒,怀揣着各自的导演梦,挤在狭小的教室里,听着老师讲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”和“场面调度”,这里有骄傲的富家子弟,拿着最新款的摄像机,谈论着欧洲电影节;也有像我一样,来自普通家庭,靠着一腔孤勇前行的“草根”,我们之间有过竞争,有过嫉妒,但更多的是惺惺相惜,我们会在深夜的宿舍里,互相点评彼此的作品,会因为一个镜头的争论而面红耳赤,也会在模拟面试失败后,拍着对方的肩膀说“没关系,下次再来”。
那段日子,是痛并快乐着的,我第一次用借来的DV机,带着剧组成员在零下五度的冬夜,拍摄一部关于城市边缘拾荒者的短片,我的手冻得通红,按不住快门,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下来,但当我看到监视器里,那个佝偻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时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,那种感觉,比任何一次模拟考的满分都更让我激动。
当省考的合格证像雪片一样飞来时,我知道,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——北电。
北电,是所有电影人心中的圣地,也是最残酷的战场,它的初试,是文史哲及艺术常识的笔试,那一题,考的是《公民凯恩》的叙事结构;那一题,问的是“库里肖夫效应”的定义,我几乎是从《电影艺术》的扉页开始,一个字一个字啃过来的,当看到题目时,我心中默念“这不是巧合,这是宿命”,然后奋笔疾书,走出考场,看到身边有人因为“声画对立”和“声画同步”的区别而抓耳挠腮时,我知道,我的坚持没有白费。
复试,是三分钟的自我介绍和回答考官提问,我准备了整整一个冬天,自我介绍,我摒弃了“我叫林风,来自XX,热爱电影”这种千篇一律的开场,而是用一段精心设计的独白,讲述了我从《罗生门》到决定报考北电的心路历程,我告诉考官,我的电影梦,不是为了名利,而是为了记录那些被时代洪流淹没的、普通人的微光。
真正的考验,在复试的问答环节,一位戴着金丝眼镜、气场强大的女考官问我:“同学,你刚才说想记录普通人的故事,那你认为,‘普通’和‘平庸’有什么区别?”
这个问题像一颗子弹,正中我的要害,我愣了一下,大脑飞速运转,我想到了我的短片,想到了那个拾荒者,想到了我的父母,我深吸一口气,回答道:“考官老师,我认为‘普通’是生活的常态,是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的、独一无二的烟火气,它可能不完美,甚至有些狼狈,但它真实、鲜活,充满了生命力,而‘平庸’,是一种态度,是一种对生活失去感知和热情的麻木,我的电影,想做的,就是去发现‘普通’中的不凡,去唤醒人们对‘平庸’的警惕,就像我的父亲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,但他用双手撑起一个家,他的爱,一点也不普通。”
说完,我看到那位女考官的嘴角,似乎微微动了一下,我不知道那是赞许还是别的什么,但我已经把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,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卸下了所有的伪装,像一个真正的导演,在阐述自己的电影观。
如果说复试是心理战,那么三试,就是一场赤裸裸的生存演练,三试是现场创作,抽到题目后,有24小时的时间,团队需要完成一部3-5分钟的短片。 是《最后一盏灯》。 我们五个人立刻开始了头脑风暴,一个来自东北的男生提议拍一个深夜值班的保安,他坚守着最后一盏灯,守护着大楼的安全,一个打扮很潮的女生想拍一个失恋的女孩,在黑夜里,只有床头灯陪着她,讨论声在宾馆的小房间里回荡,气氛一度很焦灼。
我听着,一直没有说话,直到他们声音渐歇,我才开口:“我们能不能把‘灯’的概念,再扩大一点?它不一定是一盏实体灯。”
所有人都看向我。
“我想到一个故事,”我缓缓地说,“在一个老旧的居民楼里,马上就要拆迁了,楼里住着一个孤寡老人,他舍不得走,因为这里有他老伴的回忆,拆迁队把整栋楼的电都断了,只给他家留了一盏应急灯,这盏灯,是他和这个世界的最后连接,而故事的高潮,是有一天,这盏灯也不亮了,在一片漆黑中,老人摸索着,找到了老伴生前留下的一盏煤油灯,他点亮了它,昏黄的光芒里,他仿佛看到了老伴的笑脸,最后一盏灯,不是电灯,而是人心里的那盏灯。”
我的故事讲完,房间里一片寂静,几秒钟后,那个东北男生一拍大腿:“绝了!就是这个味儿!”
接下来的24小时,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,分镜头、找场地、联系演员、准备道具,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,只能用一部单反相机,我们跑到即将拆迁的居民楼,用口香糖粘上应急灯,模拟断电的效果,扮演老人的,是我们团队里一个同学的爷爷,他听我们讲完故事,眼眶都红了。
拍摄那天,北京的寒风刺骨,我们在一个废弃的楼道里,一遍遍地拍摄老人点亮煤油灯的镜头,老人的手在抖,我们的心也在抖,当镜头里,那团小小的、温暖的火苗终于亮起时,我们所有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,那一刻,我们不再是为了考试而拍电影,我们是在用影像,完成一次对生命和记忆的致敬。
交片的时候,我们抱着那台笨重的电脑,手心全是汗,当考官按下播放键,我们五个人在门外,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。
影片放完,门开了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,走出来,看着我们,缓缓地说:“这个故事,很朴素,但是很真诚,你们拍出了光,也拍出了人心。”
那一刻,我知道,我们赢了。
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,每天刷新着招生网,看着那个空荡荡的页面,我的心就像坐过山车,直到那一天,我收到了那条短信:“林风同学,恭喜你,通过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专业考试。”
我拿着手机,站在阳台上,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,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,我想起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想起了培训教室里昏黄的灯光,想起了那个在寒风中点燃煤油灯的背影,这三千个日夜的挣扎与奋斗,在这一刻,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,顺着脸颊,滴落在脚下的土地上。
后来,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北电的校服,走进了那个我曾无数次在梦里梦见的校园,我知道,这只是一个开始,艺考的结束,不是梦想的终点,而是一条更艰难、更漫长的道路的起点。
但每当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一场老电影,每当我在片场熬夜拍到凌晨,每当我在剪辑台前为一帧画面而反复打磨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站在北电门口的冬天,想起那块冰冷的石碑,想起那场关于“最后一盏灯”的考试,想起那段光影之外、声息之间的青春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纯粹、最勇敢的一段时光,它告诉我,只要心中有光,脚下便有路,而那条通往电影圣殿的路,我,才刚刚开始走。
标签: 北电艺考3000字心酸 追梦人北电艺考故事 北电艺考酸甜苦辣经历